您当前的位置:检测资讯 > 科研开发
嘉峪检测网 2025-04-14 08:43
CD3双特异性抗体是治疗癌症的一种有前景的疗法。这些分子能够结合T细胞表面的T细胞受体(TCR)/CD3蛋白复合物上的CD3以及肿瘤细胞表面的肿瘤相关抗原(TAA)。当CD3和TAA同时被结合时,T细胞与肿瘤细胞的接近会导致免疫突触的形成、T细胞的激活以及细胞毒性的产生,造成对肿瘤细胞的定向杀伤。目前为止已经获批的TCE包括Catumaxomab(2009, CD3/EpCAM,已退市)、Blinatumomab(2014, CD3/CD19)、Tebentafusp(2022, CD3/gp100)、Mosunetuzumab(2022, CD3/CD20)、Teclistamab(2022, CD3/BCMA)、Epcoritamab(2023, CD3/CD20)、Glofitamab(2023, CD3/CD20)、Talquetamab(2023, CD3/GPRC5D)、Elranatamab(2023, CD3/BCMA)、Tarlatamab(2024, CD3/DLL3)、Odronextamab(2024, CD3/CD20)。典型的TCE结构是个三聚合物,由TCE、T细胞和肿瘤细胞组成,通过T细胞激活,释放炎症因子和细胞毒性分子,杀伤肿瘤细胞。随着CD3双特异性抗体的火热,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国内药企研发的TCE产品陆续达成多个海外交易,包括嘉和生物(CD3/CD20)、同润生物(CD3/CD19)、岸迈生物(CD3/BCMA)、恩沐生物(CD3/CD19/CD20)、维立志博(CD3/CD19/BCMA)、康诺亚(CD3/BCMA)等。再次使得TCE双抗成为行业研究的热点之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TCE在实体瘤的突破,进一步增加了这类产品的应用场景和想象空间。
那么对于CD3双抗TCE这类产品,非临床安评方面有哪些挑战呢?早在2018年的时候,FDA CDER与美国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HESI)免疫安全性技术委员会(ITC)围绕CD3双抗TCE产品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相关主题展开过一系列讨论,并以《Summary of a workshop on pre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afety assessment of CD3 bispecifics》发表,一起学习下各中观点。
CD3双抗对T细胞生物学作用的影响
来自Regeneron的Jessica Kirshner对这一主题做了分享。正常情况下,T细胞是通过TCR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pMHC)递呈的肿瘤肽段的相互作用来识别肿瘤。TCE通过同时结合T细胞上的CD3和肿瘤细胞上的TAA,使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不再依赖内源性TCR路径。而且,TCR-MHC/多肽、TCE-TAA两条路径诱导的T细胞生物学作用非常相似。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通过CD3传统的信号强度是否存在最佳情况,比如在不引发细胞因子过度释放和/或T细胞耗竭的情况下保留抗肿瘤细胞毒性?如果存在,如何通过实验确定CD3信号强度的“最佳点”?当时,在本次会议上,没有人表示他们已经确定了CD3信号强度的“最佳点”,但正在使用体外T细胞-肿瘤细胞共培养系统来探索这一可能性。不过,2021年,Amgen从Teneobio花费25亿美金买了一款保持T细胞激活的同时,不会刺激细胞因子过度释放的靶向PSMA TCE—AMG340。可惜的是,AMG340前列腺癌临床Ⅰ期的27例患者ORR为0%。2023年,Amgen停止了该产品的进一步开发。这个想法很好,保留药效,降低毒性,但其中机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
评估CD3介导的T细胞生物学作用的指标很多,包括CD3下游的信号分子(如活化T细胞的核因子、NFκB),以及T细胞激活、增殖、细胞毒性标志物和细胞因子。还可以在体外实验中评估TCE与TAA或CD3的不同亲和力以及TAA丰度对细胞的影响。
当然,大多数企业表示他们主要依赖体内试验数据进行项目决策,尤其是安全性相关的数据。除了利用天然野生型,regeneron还使用不同的人源化小鼠模型外,比如表达人类CD3信号复合体小鼠,以及将人类TAA敲入小鼠基因座,并用于支持药理学和安全性相关的研究。
肿瘤抗原表达及相关风险
与靶点相关的在靶(on-target)毒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on target/on-tumor”毒性,主要包括细胞因子释放及其相关毒性,严重程度取决于肿瘤负荷以及TCE到达肿瘤部位的能力。还有一类是“on target/off-tumor”毒性,与TAA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和分布直接相关。
由于非临床安全性测试通常不使用肿瘤疾病模型,因此“on target/on-tumor”相关的细胞因子释放通常不在非临床阶段进行体内评估,换句话说,采用健康猴或者其他种属也实现不了这一毒性的评估。取而代之的是在体外肿瘤细胞/免疫细胞共孵育体系中考察细胞因子产生情况。另外,TAA驱动的细胞因子释放在临床是可监测且可管理的。
与“on target/on-tumor”不同,“on target/off-tumor”毒性的风险评估是临床前研究的重点所在,比如正常组织中靶点分布、细胞定位和表达水平等。需要在药理学相关动物种属中开展标准毒理学研究,特别关注靶点表达相关的组织。
安进公司的Hervé Lebrec博士分享了如何评估正常组织中TAA表达和潜在风险。首先通过靶点表达的文献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初步了解靶点的表达和分布情况。然而,文献提供的靶点表达信息往往无法满足需求,这就需要借助一些试验手段和工具,比如用于mRNA分析的RNA测序、原位杂交和定量PCR,以及用于蛋白分析的western blot、免疫组化和质谱分析。而且,通常需要多种方法交叉确认,以全面、客观了解靶点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和分布情况。
同样来自安进公司的Oliver Thomas对早期靶点风险评估在预测BiTE抗体(安进的双抗平台)非临床安全性特征中的作用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猴通常是TCE非临床毒理研究中唯一相关种属。如果在猴的正常组织中存在目标TAA表达,通常在给药后48小时内会观察到一些反应,包括呕吐、活动减少、食欲不振、腹泻、短暂体温升高、急性期反应(CRP增加、球蛋白和纤维蛋白原增加、白蛋白减少)、血液学变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T细胞激活)、其他白细胞亚群的变化以及短暂的细胞因子释放(如IFN-γ、IL-6、MCP-1和TNF-α)。经历较短的暴露间隔后(约1-4周,取决于分子的活性),可以观察到更完整、全面的靶器官毒性表现。急性细胞因子释放的强度与靶点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及其特定位置有关。如果靶点在正常组织中完全不表达,则不会发生细胞因子释放;如果TAA比较容易被CD3双抗识别(如表达在血细胞上时),则细胞因子反应通常更强。CD3双抗观察到的组织病理学变化多数情况下与靶点表达相关,包括轻微到严重的混合细胞或淋巴细胞浸润、炎症和/或单细胞坏死。可以将体内毒理研究结果与靶点表达和分布特点相结合,进行适当的风险-收益评估,并考虑潜在的毒性可监测性和可管理性。
Xencor公司的Liz Bogaert博士认为,仅依赖公共数据库中的靶点序列和表达数据可能会低估猴中毒理反应。以叶酸受体1(FOLR1)这个靶点为例,其在多种正常组织中表达,包括正常肺和肾。猴中的毒性包括细胞因子释放,以及肺和肾损伤等,但观察到的剂量远低于预期。原因是体外活性试验采用的重组猴FOLR1蛋白序列引用自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的序列,而该序列与猴子中的实际FOLR1序列并不一致。直接导致了CD3双抗在猴子中的活性和毒性被严重低估。不过,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小。
分子结构、CD3和/或TAA亲和力对活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影响
辉瑞公司的Adam Root介绍了各种CD3双抗format,并认为企业在设计CD3 TCE结构时会考虑多种因素。有些考虑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如知识产权或生产可行性,另一些考虑则来自科学驱动,如T细胞与靶细胞之间的空间距离、对CD3和/或肿瘤抗原的结合价数(单价、双价或其他)、给药方案、特定的PK特性以及预期的安全性特征。例如,半衰期较短的CD3双抗在管理新出现的安全性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因为可以快速被清除,但在给药方案方面存在劣势,需连续或频繁给药。Blinatumomab就是一款结构中没有Fc的短半衰期TCE,临床需要长时间连续静脉输注给药。除了结构外,TCE与CD3的亲和力被认为是决定疗效和安全性的一个关键因素。CD3亲和力过高可能会降低系统暴露量,并将CD3双抗从肿瘤转移到含有T细胞的组织。亲和力过低则可能会降低T细胞的激活能力,影响药效。
有人提出CD3结合的动力学可能会影响细胞因子释放。也有人认为CD3结合表位不同,所引发的T细胞作用也有差异。大多数CD3双抗靶向CD3ε的N端线性肽,尚不清楚靶向不同的CD3表位是否会导致细胞毒性与细胞因子释放的比率不同。不过,前文已经提到,Teneobio开发出了具备CD3结合表位差异化的TCE,维持T细胞毒性的同时,细胞因子释放并不明显,但临床研究的失利为这一思路蒙上了阴影。
关于TAA结合效价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根据结合亲和力和结构,增加结合效价可能有利于对肿瘤的靶向和重定向,但这些潜在益处会增加CMC研究的复杂性。放至今日,CMC问题应该相对容易解决。
罗氏公司的Anna Maria Giusti博士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两个分子具有相同肿瘤靶点——FOLR1,相同构造(TAA:CD3=2:1),且两种分子对FOLR1的亲和力都高于CD3。不同的是,第一个分子对FOLR1的结合亲和力(affinity)比第二个分子高20倍以上,但由于采用了双价TAA结合,两种分子对肿瘤的结合亲合力(avidity)相似。动物毒理研究结果显示,食蟹猴给予低剂量的第一个分子(higher affinity)时,没有观察到临床症状,但10 mg/kg剂量的食蟹猴出现了不良反应,包括呼吸异常,导致在给药后24小时实施安乐死,并在肺部观察到病变(水肿、充血和急性炎症)。免疫组化显示,食蟹猴和人肺泡细胞上表达FOLR1。由于担心人体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肺部病理变化,因此开发了第二种分子,立项依据是肿瘤细胞相对于正常组织表达更高水平FOLR1,第二种分子能保留与肿瘤的类似亲合力(avidity)同时,降低对正常组织如肺部的影响。
出乎意料的是,当在食蟹猴中测试这种对FOLR1亲和力低得多的第二种分子时,观察到了与第一种分子完全不同的症状:眼睛“浑浊”与单核细胞在睫状体和虹膜浸润,前房和后房有渗出物。因此,虽然避免了第一种分子出现的肺部毒性,但观察到了一种新的毒性表现。通过IHC方法未能在眼睛中找到FOLR1,但通过定量PCR鉴定出了FOLR1 mRNA。因此,两种对靶标具有不同亲和力的FOLR1 CD3双抗显示出不同的靶点相关的毒性特征。由于两种毒性特征均不可接受,因此该项目被终止。这种“on-target/off-tumor”毒性是TCE最不愿看到,也最难避免的毒性,是这类分子开发失败的主要风险之一。
基因泰克公司的Karen Staflin博士以一个针对HER2的CD3双抗为例,展示了对CD3和/或TAA的结合亲和力对非临床疗效和耐受性的影响。由于HER2在正常组织中广泛表达,因此存在对on-target/off-tumor毒性以及细胞因子释放的担忧。构建了基于全长IgG1抗体的HER2/CD3双抗(1:1形式),并具备低Fc效应功能特点。筛选出与CD3靶点亲和力差异为30倍,HER2为7倍的不同变体进行组合。最初,将低亲和力抗HER2变体与低亲和力或高亲和力抗CD3配对。两种分子在体外对HER2阳性靶细胞表现出强大的细胞毒性,并在人HER2转基因小鼠模型中观察到体内抗肿瘤药效。然而,它们的耐受性特征不同。低亲和力CD3变体在小鼠和食蟹猴中耐受性良好,但高亲和力CD3变体在小鼠中出现细胞因子释放增加和体重减轻,以及食蟹猴出现全身性炎症反应。接下来,将低亲和力抗CD3变体与低亲和力或高亲和力抗HER2配对。在体外细胞毒性实验中,使用表达食蟹猴HER2的靶细胞时,高亲和力抗HER2的分子活性表现更好。两种分子在食蟹猴体内均产生了药理学反应,如淋巴细胞短暂减少。然而,高亲和力抗HER2变体耐受性不如低亲和力分子。研究人员通过采用剂量分割方案(第0天给半剂量,第1天给半剂量,第8天给全剂量)减轻了食蟹猴中观察到的高亲和力抗HER2变体的细胞因子释放。剂量分割导致在给药初期双抗的Cmax降低,同时又维持了总暴露量的不变。在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剂量分割显示对药效没有影响。Karen Staflin博士这个思路其实被用于很多已上市或在研TCE的设计,即高亲和力TAA与低亲和力CD3的分子进行配对,临床则采用step-up dose策略给药,降低首次给药Cmax,增加患者耐受性。
来自MacroGenics的Ezio Bonvini博士,也提到了关于将细胞毒性与细胞因子释放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类似说法,即各论各的。他列举了一系列CD123/CD3 DART结构的分子,这些分子与CD3结合表位存在差异。研究比较了CD3的亲和力、结合和解离速率与细胞毒性EC50的关系。研究发现,一种低亲和力的CD3变体在更高浓度下表现出与野生型分子相似的细胞毒性水平,但在细胞毒性相当的情况下,细胞因子释放显著减少。此外,低亲和力变体需要更高浓度才能在体外诱导T细胞增殖,以及在小鼠体内模型中需要更高剂量才能实现与野生型分子相似的肿瘤生长抑制效果,但在所有剂量水平下,包括达到最大抗肿瘤效果的剂量,细胞因子释放均减少。在食蟹猴中,低亲和力CD3变体在高达20 mg/kg的剂量下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并且暴露量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而高亲和力CD3变体在3 mg/kg剂量下就表现出细胞因子释放和较差的耐受性。此外,一种针对B细胞的低亲和力CD3变体(与CD123靶向变体共享相同的CD3结合臂)在食蟹猴中能够有效耗竭B细胞,并表现出良好的耐受性,进一步确认了靶向CD123变体的观察结果。MacroGenics的CD123/CD3 TCE(MGD024)目前处于临床Ⅰ期研究阶段,并于2022年10与Gilead达成合作,共同开发。可能有朋友会问,采用同样思路的Teneobio不是已经失败了吗,可别忘了,Teneobio开发的是实体瘤靶点,MacroGenics这个是血液瘤,TCE在血液瘤里面已经上市了很多产品,实体瘤却仅上市了2款产品,失败了不下几十个,实体瘤本身就是TCE失败的重灾区。一切还是以临床数据说话,期待MacroGenics通过CD3表位差异的设计能否在临床完成低毒、高效的概念验证。
CytomX的Jennifer Richardson博士分享了TCE中的Probody思路,这是一种抗体前药设计,使TCE在肿瘤微环境中选择性激活。简单讲,就是TCE的抗原结合区域采用遮蔽肽封闭,同时用可被蛋白酶降解的连接子偶联。这类蛋白酶在肿瘤中特异性高表达。与未遮蔽的对照分子相比,CytomX的Probody TCE在体外对正常细胞的抗原结合和活性降低,同时在某些小鼠异种移植瘤模型中药效也降低。通过使用更易被蛋白酶切割的底物,克服了小鼠中疗效降低的问题。使用较弱的CD3结合臂和更紧密的遮蔽肽提高了食蟹猴的耐受性。遮蔽肽技术有可能扩大CD3双抗的治疗窗口。不过,与会者指出,遮蔽肽技术能否提高治疗指数将取决于其在肿瘤微环境中选择性释放遮蔽肽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发生在2018年的讨论会。那么从2025年,回头看,CytomX与Amgen合作的CX-904(CD3/EGFR)、与BMS合作的CTLA-4免疫检查点前药BMS-986288相继停止开发。再次提示,前药设计不仅遮蔽那么简单,有效释放才是关键。
体内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
本部分主要围绕三个主题进行讨论:1)基因工程小鼠在安全性评价中的作用;2)食蟹猴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考量;3)无毒理学研究相关动物种属的考量。
基因工程小鼠在安全性评价中的作用
来自Dartmouth College的Charles Sentman博士展示了CD3双抗在不同小鼠模型中的疗效数据,包括在免疫缺陷的NSG小鼠中的胰腺癌模型,以及在免疫正常C57BL/6小鼠中的淋巴瘤(RMA)、转移性黑色素瘤(B16)数据等。发现,耗竭CD4+或CD8+ T细胞亚群会影响CD3双抗药效。通过基因敲除模型发现,穿孔素和IFNγ是抗肿瘤作用发挥的关键成分,但它们也与毒性的产生相关。经过治疗后肿瘤完全消退的小鼠,再次接种相同肿瘤后,抗肿瘤作用依然存在,证明CD3双抗存在免疫记忆。这些可能与TCE在开发阶段的安评相关性较小,更多提示我们可以基于基因工程改造的小鼠研究TCE药理学和毒理学相关目的的研究。
Regeneron的 Jessica Kirshner博士重点介绍了通过Velocigene技术基因工程改造的小鼠,这些小鼠CD3的位置表达人类CD3(胞外区),并在小鼠细胞上表达人TAA,即人类CD3和TAA基因的双敲入。另外,小鼠肿瘤细胞也同样导入了人TAA。为了确保模型能够达到预期的T细胞水平以及通过抗人CD3抗体对T细胞的充分激活,对转基因模型进行了表征。此外,还评估了小鼠组织中人TAA的表达,以确保人TAA表达的一致性。
Kirshner博士分享了REGN1979(CD3/CD20双抗)和REGN4018(CD3/MUC16双抗)两个案例。Regeneron的CD3双抗是全长抗体,Fc通过改造去除了效应功能。在REGN1979的案例中,人源化小鼠模型中快速出现了外周血B细胞耗竭和短暂的细胞因子释放,并抑制了肿瘤生长。同样,REGN1979给予食蟹猴后,发现了类似的B细胞耗竭和细胞因子释放。此外,对淋巴组织(如脾脏和肠系膜淋巴结)的免疫组化分析显示有深度的B细胞耗竭。在REGN4018的案例中,也使用了CD3和MUC16基因人源化的小鼠模型。小鼠的MUC16在多种具有间皮/浆膜表面的组织中表达(如卵巢、气管)。REGN4018在小鼠中诱导了抗肿瘤活性,但没有导致全身性细胞因子释放或on target/off tumor组织的病理变化。在食蟹猴中,观察到稍微不同的反应,如CRP和IL-6短暂增加。
总之,基因工程小鼠可以作为初步评估TCE分子药效和安全性的模型之一。
食蟹猴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考量
Janssen 的Shoba Shetty博士分享了一个案例,展示了通过调整CD3双抗的剂量来减轻食蟹猴中的细胞因子释放。该分子是一种针对实体瘤靶点的抗体类CD3双抗,Fc去除了效应功能。TAA在多种肿瘤类型以及某些正常组织中表达。
在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中,食蟹猴每周一次或两次的给药方案导致了急性细胞因子释放相关的剂量限制性毒性,甚至出现了动物死亡。临床症状表现为呕吐、弓背和活动减少,主要出现在首次给药后。观察到细胞因子呈剂量依赖性增加,高浓度细胞因子与死亡相关,但随着重复给药,细胞因子水平有所下降。临床病理学变化包括白细胞(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的短暂减少以及急性期反应。有趣的是,早期死亡的动物组织中未见镜检,而存活动物则表现出多组织的淋巴细胞浸润以及表达TAA器官的轻微组织退化/再生。
后续研究探索了通过低剂量预处理免疫系统,然后再给予较高剂量,以尝试减轻细胞因子介导的毒性。选择了一个初始的低剂量,预计动物可以耐受,但会产生药效学效应(如短暂的淋巴细胞减少和最小程度的细胞因子释放)。评估了两种动物体内剂量递增方案,测试的最高剂量达到了初始最大耐受剂量的10-25倍。所有动物均存活,临床症状改善,并且细胞因子(例如IL-6和TNF-α)显著抑制。
通过step-up给药方案,可以潜在解决TCE这类产品在食蟹猴毒理学研究中可能碰到的暴露量不够的问题。
Genentech的Amy Sharma分享了一个CD3/CLL-1双抗的案例研究,本品拟用于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Genentech评估了两种CD3双抗,它们与CD3的亲和力相差100倍,与CLL-1的亲和力相同。此外,两株抗体与食蟹猴靶点的亲和力均与人体相似。
研究首先在CD3和CLL-1双靶点人源化小鼠中开展,在0.5 mg/kg的剂量下,两个分子均能实现单核细胞的耗竭。不过,同样剂量在食蟹猴中不能耐受,采用的“哨兵”动物先行给药的方案。后续进行了剂量调整。发现低亲和力分子在较低剂量下,食蟹猴耐受性良好,并在第8天观察到髓系细胞最大程度的耗竭。另外,低亲和力和高亲和力分子的暴露量相似,所有动物均产生了抗药物抗体(ADA)。低亲和力分子诱导的细胞因子释放低于高亲和力分子,但两者在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耗竭程度和持续时间上相似。两种分子均表现出双相反应,急性细胞因子介导的效应在给药后24-48小时出现,而亚急性的on target/off tumor效应(如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或可能由骨髓抑制引起的继发性感染)在给药后数天出现。
这个案例给出了3条TCE毒理研究的经验:1)可以设置哨兵动物,先行给药,并对哨兵动物设置7天的观察期,以考察延迟毒性;2)基于人源化小鼠药理学研究设置食蟹猴试验的剂量时需谨慎,尤其是小鼠和猴的靶点表达谱可能不一致,且小鼠对炎症刺激的耐受更强;3)由于ADA的产生,研究持续时间受到限制,毕竟ADA的发生率很高。
辉瑞公司的Cris Kamperschroer博士分享了一个通过药理学手段影响食蟹猴中细胞因子释放和T细胞活性的案例。采用一种CD3/TAA双抗,含有去除效应功能的Fc,该TAA在上皮细胞和浆膜细胞中表达。为减轻细胞因子的影响,研究采取了三种方法:1)抗IL-6单抗;2)Janus激酶抑制剂(JAKi);3)糖皮质激素药物地塞米松(DEX)。均在CD3双抗给药前开始使用。研究终点包括血清细胞因子水平、与细胞因子释放相关的临床症状(如呕吐、活动减少和弓背)以及细胞因子诱导的急性期蛋白CRP。还评估了T细胞激活相关标志物如外周和脾脏CD8+ T细胞上的CD69表达以及可溶性CD25水平,以及对TAA阳性细胞的预期杀伤作用。结果显示,JAKi或DEX降低了某些细胞因子(如IL-6和IFN-γ)的水平,并减轻了与细胞因子释放相关的临床症状,而抗IL-6单抗则没有这种效果。尽管看到了抗IL-6单抗的药理学相关PD指标变化(表现为没有诱导CRP升高,因为IL-6诱导CRP),但其对细胞因子释放的影响较弱,这与临床上采用抗IL-6受体(IL-6R)抗体(如托珠单抗)治疗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效果相反。
在T细胞激活方面,只有JAKi抑制了T细胞上可溶性CD25和CD69的上调。组织病理学评分显示,所有细胞因子阻断剂均未避免TAA表达细胞的损伤的出现。总结来说,JAKi和DEX在抑制细胞因子释放和防止细胞因子相关临床症状方面是有效的,而抗IL-6单抗则无效。所有细胞因子阻断剂未影响T细胞对组织中表达TAA细胞的活性,但JAKi抑制了T细胞激活标志物的上调。
正是由于JAKi也影响了T细胞激活,因此DEX被认为是预防CRS的最佳选择,既降低细胞因子相关毒性,又不影响T细胞激活和杀伤。当然,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在临床上治疗或预防CRS的潜在选择。由于毒理研究的目的是表征分子的潜在安全性风险,这其中就包括与细胞因子释放相关的风险,因此不推荐在非临床毒理研究中进行药理学手段的干预,这本身就会引入新的变量,使整项研究更为复杂。还是建议采用Janssen 的Shoba Shetty博士推荐的动物体内剂量递增方案。
来自Janssen的Chidozie (Dozie) Amuzie博士讨论了接受CD3双抗治疗的食蟹猴中观察到的组织病理学变化。伴随CRS症状的食蟹猴,镜下发现包括多器官的单核细胞浸润和血管炎症。其中,血管炎症不应与血管和血管周围免疫细胞浸润混淆。TCE免疫细胞浸润位于小至中等大小动脉的周围和壁内。这与由单克隆抗体或反义寡核苷酸诱导的血管炎症所观察到的血管壁增厚或破坏明显不同。
Amuzie还分享了一些与CD3双抗相关的特定组织中的免疫细胞浸润案例。例如,一些非CD19靶向的CD3双抗,观察到脑部单核细胞浸润(MNCI)。虽然在对照动物中也可以观察到MNCI,但通常位于蛛网膜下腔和脑膜的软脑膜之间,而CD3双抗对应的MNCI深入脑实质和神经纤维中,且浸润更为密集。通过原位杂交技术鉴定,脑部的MNCI主要由T细胞组成。不过,这些动物并未表现出任何神经系统相关的症状。
肾上腺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器官,尤其是出现严重急性反应的动物,皮质中观察到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并与细胞因子释放相关。当使用不同的给药方案(如增加给药频率)时,肾上腺髓质中可以看到密集的MNCI。其他在较高不耐受剂量下观察到镜检变化的器官主要是肾脏和肺。肾小管变性/再生最早可在初次给药后24小时内检测到。当然,肾脏毒性的最终定性还要结合BUN或肌酐等其它指标综合判定。
无毒理学研究相关动物种属的考量
Immatics公司的Frank Schwöbel博士回顾了该公司CD3双抗的非临床研究策略。这种双抗由抗CD3 scFv(单链抗体片段)和识别肿瘤抗原肽/白细胞抗原(HLA)复合物的单链TCR(scTv)组成。Immatics的XPRESIDENT平台拥有一个庞大的肽-HLA信息数据库,能够揭示40多个不同器官肿瘤与正常组织之间所递呈的肽段差异。由于HLA具有高度的种属特异性,传统的体内动物研究并不适用于临床前安全性评估。Immatics曾考虑使用HLA-A*02转基因小鼠,但发现这些小鼠有以下不足:1)抗原处理的差异;2)人与动物蛋白序列的差异;3)人与动物基因表达谱的差异。因此,临床前安全性评估主要基于计算机模拟(in silico)和体外(in vitro)测试。比如,会评估双抗对正常组织上表达的相似序列肽段的潜在交叉反应性,以及与TCR结合相似肽段的交叉反应性。此外,还会针对靶点阴性的肿瘤细胞和原代健康组织细胞panels进行功能测试。这些数据与针对靶点阳性肿瘤细胞的体外药效实验结果进行比较,以计算治疗窗口。
Immunocore的Joseph Dukes博士分享了该公司开发的CD3 TCE,也是由抗CD3 scFv和识别MHC/抗原肽(pMHC)的TCR组成。CD3结合域具有纳摩尔级别的亲和力,而pMHC结合域经过亲和力成熟,达到皮摩尔级别的亲和力,旨在能够识别细胞表面极低数量(10-100个)的表位。
由于CD3和pMHC结合域均只针对人,没有合适的毒理相关种属。Immunocore曾考虑使用HLA转基因小鼠,但情况与Immatics遇到的类似,由于肽段中常见的跨种属点突变(通常会破坏TCR结合),以及数据显示转基因小鼠中超过60%的HLA呈递肽段缺失,使得在该模型中评估pMHC结合域的特异性没有价值。因此,Immunocore开发了一套基于人类的in silico和in vitro的测试方案,用于预测临床安全性和特异性。In silico方案利用内部数据库中的pMHC肽段,评估特定TCR与其他pMHC的潜在交叉反应性。体外安全测试方案包括对约100种细胞系(覆盖约20个器官的50-60种组织类型)进行了测试,如评估异体反应性、血小板激活、全血中的细胞因子释放以及正常人类组织中目标肽段和蛋白的表达。
大部分安全性测试涉及使用原代细胞、人T细胞和TCE分子进行共培养,并建立合适的检测指标,如T细胞激活、IFN-γ或颗粒酶B的产生,或靶细胞杀伤。这些体外实验还用于基于MABEL法确定首次人体(FIH)剂量。
首个进入临床开发的分子是IMCgp100,其靶向由HLA-A*0201呈递的gp100280-288肽段,该肽段在正常皮肤和眼睛的黑色素细胞以及黑色素瘤(尤其是葡萄膜黑色素瘤)中表达。体外数据显示,在1纳摩尔浓度下药物无脱靶效应,最大药理效应出现在100皮摩尔浓度,MABEL被确定为1皮摩尔。针对正常黑色素细胞的活性预计在皮摩尔范围内,基于本品的作用机制,预计会出现皮肤毒性以及细胞因子介导的促炎反应。实际上,在葡萄膜黑色素瘤的I期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毒性与预期一致,包括皮疹、瘙痒、细胞因子释放、发热、低血压、恶心和疲劳。此外,随着重复给药,毒性有所降低,因此实施了患者内剂量递增,以实现更高暴露量,保障疗效。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眼睛中存在目标靶点,临床上尚未观察到葡萄膜炎。本品已经获批上市。
Roche的Estelle Marrer-Berger博士也分享了pMHC/CD3这类分子in silico和in vitro评价方法的使用。与前述内容,大同小异,不再赘述。
细胞因子释放体外测试
TGN1412是一种CD28超激动剂,在2006年3月进行的健康志愿者I期临床试验中,所有受试者均出现了严重的、危及生命的CRS,部分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并推动了体外细胞因子释放(CRA)试验方法的开发,并成为TCE分子IND enabling阶段必须要开展的关键研究之一。
杨森公司的Daniel Weinstock博士称,杨森最初为所有在研的抗体类生物药物开发了一种固相法,检测CRA。然而,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CD3双抗,因为CD3能够有效交联,固定化的CD3双抗检测通常呈阳性,无论靶细胞是否存在。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杨森开发了一种新的液相法,使用稀释1:10的人全血进行检测。在该实验中,如果全血中有TAA表达,CD3双抗会引发浓度依赖性的细胞因子释放反应。也可以考虑将细胞因子释放检测纳入细胞毒性实验中开展。
安进公司的Matthias Friedrich博士分享了该公司在CRA方面的经验。他指出,在使用分离的人T细胞进行的实验中,无论是液相法还是固相法,在没有靶细胞的情况下均未引发CRS。安进公司目前倾向于在T细胞依赖性细胞毒性(TDCC)实验中测量细胞因子释放。实验中使用了人和食蟹猴的效应细胞,如果可行,会使用患者来源的肿瘤细胞和自体T细胞(如TAA表达外周血)进行检测。但体外试验的人体预测能力有限,猴体内细胞因子释放与人体更相关。
然而,有与会者提出,对于CD3双抗,细胞因子释放是其预期的药理学作用的一部分。既然如此,为何要对已知的且风险明确的分子进行风险识别检测?FDA的一位代表表示,只要风险已知且在其他研究(药理学或毒理学)中得到确认,则无需进行单独的CRA。另一位FDA代表指出,当T细胞激活的原因不明时,通常会要求对免疫调节剂进行CRA,而CD3双特异性抗体的细胞因子释放风险已知,因此通常不需要类似Stebbings-like的C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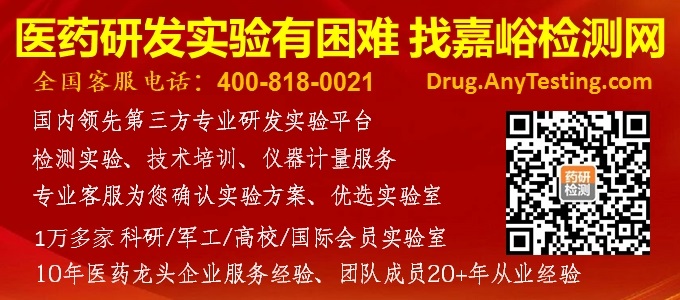
来源:药理毒理开发


